,则后天无所依托,故常有婴儿早死,儿童夭折,未老先衰之事发生,此先天不足,无论如何补充后天,皆毫无用处,反促其速死。丹经有云:“若将有形成变化,细酒羔羊亦上升”。只有补充先天无形之生气,才是根本。我中华丹道,最伟大之处就在于补充先天。
于层次来说,无缘因,无条件的自虚无中而生,曰先天,故不落因果,先天而天不敢违也。丹经云:“不忆过去,不思未来,不拟现在,三心皆无”,无为而为,佛经有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皆对先天及如何进 先天而说之。有中生有,思忆存想而得,有为而为,落于因果,称之为后天,故为天命所制,天生之必天杀之,有生有死,有命有运,是宿命的。
先天而说之。有中生有,思忆存想而得,有为而为,落于因果,称之为后天,故为天命所制,天生之必天杀之,有生有死,有命有运,是宿命的。
果真穷究至无上之根源,先天即后天,后天即无天。先天后天,言语道断,心行灭处(另,先天后天于丹道另有特别意义)。
第二节动静之说
动分阳动与 动,由中和趋于生长的运化称之为阳动,有放
动,由中和趋于生长的运化称之为阳动,有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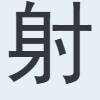 发散之意。由中和向衰败及死亡,归
发散之意。由中和向衰败及死亡,归 于寂静的动,称之为
于寂静的动,称之为 动,有收缩之意。静也分阳静与
动,有收缩之意。静也分阳静与 静,一为觉照合一之静,一为顽空,死寂之静。动若无静主
静,一为觉照合一之静,一为顽空,死寂之静。动若无静主 其中而制之,则其动变大,成为亢阳,不可收拾,最终走向死亡。而静若无动包之,则无以畅通和顺,而其神不清明,必
其中而制之,则其动变大,成为亢阳,不可收拾,最终走向死亡。而静若无动包之,则无以畅通和顺,而其神不清明,必 昏沉,成为浊
昏沉,成为浊 ,大事坏矣。故丹经有云:“以铅制汞,以息运神”。丹道修炼必须动静相得、相宜。况绝大多数
,大事坏矣。故丹经有云:“以铅制汞,以息运神”。丹道修炼必须动静相得、相宜。况绝大多数 ,皆是动特多,而静少之又少,其神纷芸变动,未能定止,
,皆是动特多,而静少之又少,其神纷芸变动,未能定止, 夜
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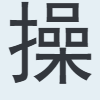 劳,无而了时,一时之内,念起念灭,心随物转,本我已迷。故吾
劳,无而了时,一时之内,念起念灭,心随物转,本我已迷。故吾 之神,
之神, 为外物所夺,神去,气亦随处,神气
为外物所夺,神去,气亦随处,神气 耗,趋于死亡。而吾
耗,趋于死亡。而吾 身体也
身体也
 奔波,被物所使,神气更失,必以静来制之,故丹道
奔波,被物所使,神气更失,必以静来制之,故丹道 门之始,必以静主之,明白静之含义,静者在于“安”,在于“无念”,在于“休息”,静*功之道,即是告诉
门之始,必以静主之,明白静之含义,静者在于“安”,在于“无念”,在于“休息”,静*功之道,即是告诉 们最佳休息方法而掌握之,“动”用于炼气,动者在于“和顺”,在于“连续而不滞碍”,无一丝间断,庄子云:“神无隙,乃成纯气之守”,放
们最佳休息方法而掌握之,“动”用于炼气,动者在于“和顺”,在于“连续而不滞碍”,无一丝间断,庄子云:“神无隙,乃成纯气之守”,放 火不焚,
火不焚, 水不溺,刀兵不能害。此为气长生。又“安”之意在于自然,安于连续之动而无念,所谓一灵独存是为真神,丹经而云:“内炼之道,全在于绵绵若存,勿忘勿助”。
水不溺,刀兵不能害。此为气长生。又“安”之意在于自然,安于连续之动而无念,所谓一灵独存是为真神,丹经而云:“内炼之道,全在于绵绵若存,勿忘勿助”。
本门认为:“无绝对静止,也无绝对运动”,任何运化和动机,都必需一“静止”的背*景场所,以此暗暗隐含的无形“静止”来允许“运化”之存在和成立,此遍一切之处的“静止”即为大道一体同观之“觉照”,寂然不动,无形无象,无我之“真观”也。静与动本一体,实不可分,由静才能体现动机、化机、丹道之要,在于静以得之,无静、无以察动,无静无以制动,丹道所有妙处之产生,都来源于一“静”。只有“静”才能做到顺其自然,才能主宰命运,因命运本身是一种运动变化也,故修真圣典《 符经》云:“圣
符经》云:“圣 知自然之道不可违,故制之以至静之道”,丹经有云:“其静曰元神,其动曰真意”。
知自然之道不可违,故制之以至静之道”,丹经有云:“其静曰元神,其动曰真意”。
修炼之士,使此后天纷芸变化之各种识神归于寂然不动之元神,使后天粗短、急促、间断之呼吸归于细长连续无滞之真息,使形体不再奔忙劳累,归于静养休息之状态。如是神亦归于身,气亦归于身,神气形浑同一体,归于吾未生之前的“形态”,神气相抱,不分彼此,化为一气,于吾之祖气想吸相连相应,则玄牝立焉,玄关成矣。动静合一,
 合一,
合一, 命合一。
命合一。
第三节天地 三者的关系
三者的关系
何谓天,浑万物而为一者曰天;分万物而为二者曰地;合万物而为三者曰 。天乃无形之天,地乃有实之地,
。天乃无形之天,地乃有实之地, 乃
乃 阳相间之
阳相间之 ,
, 本于地而生于天,故
本于地而生于天,故 身亦是一小天地,
身亦是一小天地, 身之气候亦同于天地气候之规律,故《
身之气候亦同于天地气候之规律,故《 符经》有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符经》有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天理即地理, 心即天地之心,天机应于
心即天地之心,天机应于 机,
机, 机反于天地之机,
机反于天地之机, 身之真造化,无不合符天地之自然造化,凡
身之真造化,无不合符天地之自然造化,凡 不能直接察之,唯道
不能直接察之,唯道 知之,天地之冬至,必应于
知之,天地之冬至,必应于 身之冬至,天地之夏至必应于
身之冬至,天地之夏至必应于 身之夏至,凡
身之夏至,凡 后知之,故称后天,道
后知之,故称后天,道 先觉之,故曰先天。行者果能修至自然而然之天然层次,则
先觉之,故曰先天。行者果能修至自然而然之天然层次,则 身内外之
身内外之 气之运化规律无不具一定之韵律而与天地气候真消息相契,合符一定的运行规迹和运化内景。否则,说明炼已不纯,心
气之运化规律无不具一定之韵律而与天地气候真消息相契,合符一定的运行规迹和运化内景。否则,说明炼已不纯,心 未清。又如,上半月,
未清。又如,上半月, 之无形气机趋于旺盛,此时应上弦月逐渐明朗、圆满,在此一阶段,
之无形气机趋于旺盛,此时应上弦月逐渐明朗、圆满,在此一阶段, 之
之 天也象中天宝月一样,逐渐明朗、清醒,
天也象中天宝月一样,逐渐明朗、清醒, 神也振奋起来,而下弦月则反之,
神也振奋起来,而下弦月则反之, 之气机和本
之气机和本 易
易 混浊和衰减,其中玄妙虽言语难说之,但修行之
混浊和衰减,其中玄妙虽言语难说之,但修行之 自心能觉之,故丹经有云:“有
自心能觉之,故丹经有云:“有 问我修行路,遥指天边月一
问我修行路,遥指天边月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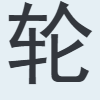 。”炼已
。”炼已 纯,
纯, 地极其洁净,就如天上无一丝云,而一
地极其洁净,就如天上无一丝云,而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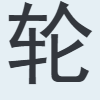 明月常悬空中,无形无相之真气候自得之,不假丝毫作为矣,就怕
明月常悬空中,无形无相之真气候自得之,不假丝毫作为矣,就怕 “
“ 心不死”,而“道心难生”。又如太阳之周期变化,太阳系之黄道应于
心不死”,而“道心难生”。又如太阳之周期变化,太阳系之黄道应于 身之黄道,天地将雨未雨,将雷未雷之氲氤气象亦有合于
身之黄道,天地将雨未雨,将雷未雷之氲氤气象亦有合于 身之氤氲气机,天地有“子”时,
身之氤氲气机,天地有“子”时, 身亦有“子”时,此天
身亦有“子”时,此天 之机的相应,不差毫发,
之机的相应,不差毫发, 身一“小天地”也,真能达到天
身一“小天地”也,真能达到天 合一之极则,行者将与天地之
合一之极则,行者将与天地之 ,天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