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开五眼神通的 ,才知道龙的真面目。
,才知道龙的真面目。
不过,中国 所画的龙,
所画的龙, 上有角,身上有鳞,眼睛突出,嘴
上有角,身上有鳞,眼睛突出,嘴 很大,有胡须,有四足,身很长,尾很短。画龙的
很大,有胡须,有四足,身很长,尾很短。画龙的 ,只画龙
,只画龙 不画龙尾,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表示有神秘之感。
不画龙尾,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表示有神秘之感。
《证异录》的最后,炼烟祖师给了这样的结语:“诸多实证查考,龙之一说似乎较之金丹成仙更接近真实一步,可仍无法铁板定案。失望之余,也让炼烟族 更加专心丹药弃永生而择长生一途。”
更加专心丹药弃永生而择长生一途。”
从种种迹象看,建造地室和整理族谱的最后一代祖师,应该是距今四百多年的明朝 。作为那个时代、那个文化背景的古
。作为那个时代、那个文化背景的古 ,能说出以上如此中肯的话,实在难能可贵。
,能说出以上如此中肯的话,实在难能可贵。
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上从皇帝下到百姓,几乎没有一个 不认为“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不认为“龙”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不要说古 ,看完《证异录》后,连思想原本反叛现代的朝歌,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神话的看法了。
,看完《证异录》后,连思想原本反叛现代的朝歌,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神话的看法了。
因为从当代公认大德高僧宣化上 的亲身证言看,他几乎没可能用自己的名誉来欺骗世
的亲身证言看,他几乎没可能用自己的名誉来欺骗世 。
。
况且从考古院研读考古资料中,朝歌也
 体会到古
体会到古 做学问的态度,远比现代
做学问的态度,远比现代 认真严谨。
认真严谨。
虽说在很多地方给未知事物蒙上许多神话色彩,但绝非空 来风、捕风捉影,其背后一定是有现实依据的原形。
来风、捕风捉影,其背后一定是有现实依据的原形。
那么,如果如此传奇神物般的龙是真实存在过的话,是否就可以侧面证明神仙的可能 呢?
呢?
朝歌一时心绪有点亢奋,又有点 。静静调息一阵后,才拿起了最后一本奇闻《证药录》。
。静静调息一阵后,才拿起了最后一本奇闻《证药录》。
《证药录》是对天下奇药异 的记载考证,因为炼烟氏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炼就长生丹,所以其中考证对象主要有三类─
的记载考证,因为炼烟氏最终想要达到的目标是炼就长生丹,所以其中考证对象主要有三类─ 参、何首乌、灵芝。
参、何首乌、灵芝。
论 参第一:山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土质过于
参第一:山参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土质过于 燥不行,过于
燥不行,过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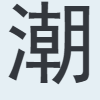 湿不行,太阳晒到不行,不见阳光不行,大雨浇淋不行,湿度不够不行,必须是伐掉树木以后的腐殖土才最好。所以上品野山参只适合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生长。
湿不行,太阳晒到不行,不见阳光不行,大雨浇淋不行,湿度不够不行,必须是伐掉树木以后的腐殖土才最好。所以上品野山参只适合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生长。
总而言之,能出上品老参的地方,一定也是上品风水宝地。而此风水宝地的 位、
位、 形、土质、水品,又决定了
形、土质、水品,又决定了 参的五行所属,只有详细摸清了
参的五行所属,只有详细摸清了 参的内在属
参的内在属 ,才能在炼药时配伍得当,否则只能发挥
,才能在炼药时配伍得当,否则只能发挥 参功效的万分之一。
参功效的万分之一。
世间常见富贵 家服食宝参不究属
家服食宝参不究属 ,实为
,实为 殄天物,如同有
殄天物,如同有 得了一万颗绝品珍珠,却随便买了一根萝卜炖汤喝了。
得了一万颗绝品珍珠,却随便买了一根萝卜炖汤喝了。
看到这里,朝歌总算明白,为什么每匣 参里面都在那张特制古宣纸上,详细记录了
参里面都在那张特制古宣纸上,详细记录了 参的各项指标,原来竟是方便后
参的各项指标,原来竟是方便后 详细辨清
详细辨清 参属
参属 ,以便在炼制长生丹时让
,以便在炼制长生丹时让 参能发挥最大功效。
参能发挥最大功效。
小小的一棵 参,从发芽、成长、被发现乃至到挖掘,都充满了玄而又神的传奇,朝歌一时好奇,去药室中打开了几匣
参,从发芽、成长、被发现乃至到挖掘,都充满了玄而又神的传奇,朝歌一时好奇,去药室中打开了几匣 参,展开熟宣古纸,每张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尤为新奇。
参,展开熟宣古纸,每张都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尤为新奇。
元代初期,有 竟在长白山森林中的大树上,发现了一棵茁壮生长的野山参,使采参
竟在长白山森林中的大树上,发现了一棵茁壮生长的野山参,使采参 感到万分惊奇。
感到万分惊奇。
因为从以往上千年的记录中,还从没有过树上长 参的记录,因为
参的记录,因为 参对土质的要求太苛刻了。
参对土质的要求太苛刻了。
采参 就爬上大树,仔细观察,只见
就爬上大树,仔细观察,只见 参长在树
参长在树 与树枝相
与树枝相 的小
的小 里,
里, 内有树叶腐烂而成的腐殖土。
内有树叶腐烂而成的腐殖土。
随之一个疑问困惑住了采参 :是谁将山参种子种到这小树
:是谁将山参种子种到这小树 里的呢?
里的呢?
后来经过仔细勘察,在这棵大树的根土里竟然挖出许多 骨来。
骨来。
从山民那里多方探听后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传说,就在这附近曾经居住过从远地迁居来的一户采参 ,据说采参的本事是祖传的非同一般。
,据说采参的本事是祖传的非同一般。
可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迁居此地后,这户祖传采参 家竟然终其三代
家竟然终其三代 也没挖出一棵
也没挖出一棵 品的老参。
品的老参。
也许是无颜再回故乡,也许是心有不甘,这户 家三代
家三代 都葬在了此地,没准,这棵长了奇参的树下骸骨就是这户
都葬在了此地,没准,这棵长了奇参的树下骸骨就是这户 家的。
家的。
由此便产生了另一个盛传之说:这棵老树奇参,是采参 三代不甘失败的魂灵守护而成,夺天地造化,吸
三代不甘失败的魂灵守护而成,夺天地造化,吸 月
月 华,参成之
华,参成之 ,既是三代
,既是三代 升天之时。
升天之时。
由此,这棵老树奇参便成了神物。
后来此参辗转被炼烟氏得到,为求究竟,炼烟氏还曾对这棵奇参做了认真实地考证,却得到另外一个可能的猜测。
据考证分析,把种子种到树 里的种参者,很有可能是
里的种参者,很有可能是 参鸟,
参鸟, 参鸟
参鸟 吃
吃 参果,吃后将参籽拉出来恰巧便到树
参果,吃后将参籽拉出来恰巧便到树 里。
里。 内有树叶、杂
内有树叶、杂 烂成的土,加上适量的雨水和树浆,则长出
烂成的土,加上适量的雨水和树浆,则长出 参来。
参来。
也有可能是松鼠、花栗鼠所为。
花栗鼠也特别愿意吃 参果,它们只能消化
参果,它们只能消化 参果的外皮果
参果的外皮果 ,而果
,而果 里面的
里面的 参籽则被排出体外。
参籽则被排出体外。
花栗鼠常在树上生活,将 参籽碰巧拉到树
参籽碰巧拉到树 里也是可能的。
里也是可能的。
 参籽特别怪,只有经过鸟、鼠的腹中走一次进行“发酵”才能出苗生长,否则还不出芽。
参籽特别怪,只有经过鸟、鼠的腹中走一次进行“发酵”才能出苗生长,否则还不出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