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 婿花锦明便远远不如了。
婿花锦明便远远不如了。
“甚好。鲁兄,贤侄底子甚是扎实。”曹延轩恭维鲁惠中,“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鲁常宁喜笑颜开地,怎么看侄儿怎么顺眼,“正是贤弟这话,我在惠中这个年纪,还惦记着喝酒吃 ,若不是夫
,若不是夫 督着,早就和惠中他爹收收账,开开铺子,谁去读劳什子四书五经!”
督着,早就和惠中他爹收收账,开开铺子,谁去读劳什子四书五经!”
曹延轩哈哈大笑,曹惠中低着 ,肩膀一耸一耸。
,肩膀一耸一耸。
鲁常宁又滔滔不绝地夸奖起侄儿来,“用我爹的话说,这孩子脑子像我, 子随他爹,若用到正处,比我和他爹都强。我夫
子随他爹,若用到正处,比我和他爹都强。我夫 也说,惠中刻苦沉稳,比我那时候强得多。我只盼着,
也说,惠中刻苦沉稳,比我那时候强得多。我只盼着, 后我那小子,能有惠中一半就心满意足。”
后我那小子,能有惠中一半就心满意足。”
说的是他七岁的小儿子。
曹延轩也说起宝哥儿:“只比你家小子大一岁。五岁我就给启蒙,前年他娘去世,吓着了,我没办法,只讲些浅显的,什么都不敢教了,就这样,
 跟着我睡,今年到了京城,方去了堂哥的院子。”
跟着我睡,今年到了京城,方去了堂哥的院子。”
又说:“他姐姐已经成了亲,等他娶了媳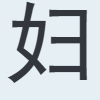 ,我也算对得起他娘了。”
,我也算对得起他娘了。”
提到珍姐儿,鲁常宁不提花家,只问“调理的如何了?孩子可好些?我家在京城 生地不熟的,连襟(赵侍郎)有相熟的大夫。”
生地不熟的,连襟(赵侍郎)有相熟的大夫。”
聊起家长里短,子 学业,两个老父亲说不完的话,
学业,两个老父亲说不完的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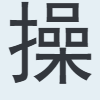 不完的心。过半
不完的心。过半 ,鲁常宁又羡慕起他来:“还是你好,已经做了外公,我像你这个年纪才有了大妞儿,孙子早着呢。”又说起侄儿:“他也是,高不成低不就,把他爹和我愁的。”
,鲁常宁又羡慕起他来:“还是你好,已经做了外公,我像你这个年纪才有了大妞儿,孙子早着呢。”又说起侄儿:“他也是,高不成低不就,把他爹和我愁的。”
曹延轩道:“贤侄这么好的 品,年纪轻轻有了功名,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
品,年纪轻轻有了功名,怎么会找不到合适的 家?”
家?”
鲁常宁咳一声,“不怕贤弟见笑,我家不如连襟,在老家算不上高门大户。自我过了乡试,惠中读书有了眉目,家里眼光高了,盼着给他找个读书 家的姑娘,就没着急。待惠中过了乡试,家里喜得不行,开始找
家的姑娘,就没着急。待惠中过了乡试,家里喜得不行,开始找 家,亲戚朋友里面没什么合适的 ,主动上门说亲的,我们家看不上,我们家看上的,
家,亲戚朋友里面没什么合适的 ,主动上门说亲的,我们家看不上,我们家看上的, 家又觉得不合适。”
家又觉得不合适。”
“好不容易,我有个同窗家有个待嫁的 儿,我和惠中父亲觉得好,我夫
儿,我和惠中父亲觉得好,我夫 和惠中母亲又不肯了:那姑娘什么都好,就是个
和惠中母亲又不肯了:那姑娘什么都好,就是个 ,咳,个
,咳,个 矮了些。”
矮了些。”
听到这里,曹延轩扭 望去,鲁慧中穿一件家常青布袍子,双手扶膝,在椅中坐得端端正正--虽然坐着,也不比自己和鲁常宁矮多少。
望去,鲁慧中穿一件家常青布袍子,双手扶膝,在椅中坐得端端正正--虽然坐着,也不比自己和鲁常宁矮多少。
一句话,这年轻 的个
的个 ,确实高了些。
,确实高了些。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他便安慰道:“因缘天定,我家大姐儿的婚事是她娘定的,小 儿为着守孝,还没影子呢。”
儿为着守孝,还没影子呢。”
说到这里,曹延轩忽然一顿:鲁常宁这话,是特意说给自己的吗?
再一回忆,鲁夫 和赵侍郎夫
和赵侍郎夫 登门拜访那天,是见了媛姐儿的--曹延轩
登门拜访那天,是见了媛姐儿的--曹延轩 常习武,是个高个子,媛姐儿的母亲于姨娘身强体健,比王丽蓉、夏姨娘高出一截,媛姐儿也比几个堂姐、珍姐儿都高,超过曹延轩肩膀了。
常习武,是个高个子,媛姐儿的母亲于姨娘身强体健,比王丽蓉、夏姨娘高出一截,媛姐儿也比几个堂姐、珍姐儿都高,超过曹延轩肩膀了。
想到这里,他又一想,自己和鲁常宁一见如故,数月之间并未提及儿 之事;前
之事;前 花家的事尘埃落定,自家平安无恙,鲁常宁今
花家的事尘埃落定,自家平安无恙,鲁常宁今 便请了自己来家里。
便请了自己来家里。
想到这里,他不动声色地和鲁常宁闲话喝茶,下了两盘棋,时候也就不早了。
鲁常宁拉着他不放,告诉侄儿“告诉你婶娘,做些拿手的,再给你曹叔叔身边的 说一声。”
说一声。”
鲁惠中应了,给两 行了礼便出去了,不一时回来,“婶娘叫开一坛好酒。”
行了礼便出去了,不一时回来,“婶娘叫开一坛好酒。”
是个灵活的,看着也踏实,曹延轩心里赞道,觉得比几个侄子、大 婿不差。
婿不差。
傍晚回到家里,他去了伯父的院子,一边听朝堂之事,一边把鲁家的事当闲话讲了。
曹慷有些意外,再一想,捻须笑道:“鲁家根底薄了些,好在,还有个赵侍郎。”
鲁家如今才出了两个读书 ,比不上诗书传家的曹家,倒是赵侍郎是读书
,比不上诗书传家的曹家,倒是赵侍郎是读书 家。
家。
他也笑道:“可不,若事 成了,他们家必定善待媛姐儿。”又由衷称赞:“旁的不说,那个鲁惠中确实是个好苗子。”
成了,他们家必定善待媛姐儿。”又由衷称赞:“旁的不说,那个鲁惠中确实是个好苗子。”
上回鲁家拜访,只带了鲁常宁赵侍郎的孩子,鲁惠中没上门来,还是曹延轩曹延吉带着博哥儿齐哥儿琳姐儿回拜的时候见到的。曹慷便说:“既这么说,过一阵找个机会,让那孩子上门来,我们看一看。若真是个好的,媛姐儿年纪也不小了。”
伯父的意思,曹延轩是明白的:鲁惠中父母是商贾,未来要靠鲁常宁,赵侍郎远了一层;曹延轩是庶吉士,媛姐儿却是庶 ,又是婢生
,又是婢生 ,一些门当户对的
,一些门当户对的 家不愿意,上赶着的
家不愿意,上赶着的 家又另有所图。
家又另有所图。
曹延轩把今 的
的 形细细说了,“我看着,上回鲁赵两家来过,鲁兄有了这个意思,等着花家的事
形细细说了,“我看着,上回鲁赵两家来过,鲁兄有了这个意思,等着花家的事 有了结果,今
有了结果,今 便找了我去。”
便找了我去。”
鲁常宁今 并没当面提亲,只是把意思含蓄地表达出来,这样一来,若曹延轩觉得鲁惠中不错,回家商量了,待媛姐儿出了孝
并没当面提亲,只是把意思含蓄地表达出来,这样一来,若曹延轩觉得鲁惠中不错,回家商量了,待媛姐儿出了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