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市场,街边报亭里摆满了封面靓丽的外文杂志,电影院里有从美国好莱坞空中邮递过来的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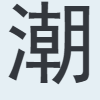 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大片……总之,从外表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与当今世界相比没太多差距的摩登时代。
很多追求小资 调的
调的 ,从林徽因、张
,从林徽因、张 玲、郁达夫等
玲、郁达夫等 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
的文章中,想象出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多种多样,
 自由解放的
自由解放的 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漫时代,并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小资风格。
但是,我们 类毕竟是不能只靠
类毕竟是不能只靠 漫和
漫和 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
调来生活的。当时租界里的小资文 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们,生活压力其实一点都不比当今社会的白领们低,而生活水平还远远不如现在。
举个例子来说,沈从文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民国时代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机关做小职员; 的北京
的北京 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
子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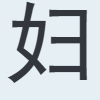 ,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生了4个孩子。在当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想必肯定是在某个很有油水的单位里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十倍,饶是这位男 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
已经很能挣钱,他们这对小资夫妻的 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
子依然很窘迫——由于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他们一家六
 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
不得不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隔开,另外半间住着沈从文,平摊下来连20个平方米都没有。而就连这么半间公寓,由于地段比较好,当时都要收每月13元的房租(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每个月的收 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
就去了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
 ,就已经用得
,就已经用得 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光,结婚八年了都还剩不下什么钱。
——在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一度电平均要收0。3~0。5银元,相当于如今的12元到20元,显然是贵得多了。幸好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冰箱、微波炉这些耗电大件,光是照照电灯听听收音机,应该还能凑合。
所以,那年 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
的小资们别看出门就是西装革履,金丝眼镜,一块流利洋文。偶尔还会出席一些宴会,跟西洋 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
子跳跳舞,生活得貌似很时尚。但真正回到家里,恐怕多半还是住着亭子间,吃着咸菜泡饭, 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顶还挂着小孩的尿布……也就跟当代的“蜗居”、“蚁族”差不多。若是再穷一点,就要去闸北住棚户了。
当然,比起江浙乡下那些连米饭都吃不起,只能啃地瓜 度
度 ,还要担心农民
,还要担心农民 动的
动的 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
产地主,上海的“蚁族”们已经很幸福了——虽然能混上教授的小资文 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们明显还要更幸福。
但这样窘迫的生活,毕竟没多少 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
愿意一直过下去,尤其是当他们还身处于上海滩这样一个花花世界的时候。很多稍微有点积蓄的上海市民,就跟现代的我们一样,纷纷把积蓄投进了 票
票 易所,企图一夜
易所,企图一夜 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
富,但结果却往往是血本无归——资本主义的信条,就是骗轻信 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
之财,填贪婪者之欲。散户和小户在 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
市中永远是被大户和庄家宰割的对象。清末的“橡皮 票危机”,1922年的
票危机”,1922年的 票泡沫
票泡沫 灭危机,让上海的
灭危机,让上海的 民们全都吃足了苦
民们全都吃足了苦 。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
。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让 产
产 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民们自杀后的尸体漂满了黄浦江……
除了 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票之外,当时还有另一个能够获利的投资渠道,就是政府债券。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以及各地军阀大帅,都乐衷于在上海发行公债募集资金,而且往往打折发放,也就是一百元的债券只卖七八十元,到期之后却能连本带利给你返还一百二十元,貌似十分优厚。
但是不要忘了,民国年间的政府工作重点,基本上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所以这些公债并非我们如今买到的建设债券,而是风险极高的战争债券。北洋政府本身都是在战火之中三天两 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
倒台重组,政府的威信自然要大打折扣。投资家买了胜利一方的债券自然收益不错,可如果不慎买了战败一方的债券,那么就注定要变成一堆废纸了—— 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家都已经倒台下野了,你的债券又该去找谁兑付呢?
当时的中国每逢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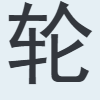 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
军阀大战落幕,上海滩都有一群失意的投机客要跳楼——当然,如果是穿越者的话,或许可以凭借对历史的先知先觉,在债券市场上大获 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利,甚至谋得一个“投资之神”的称号。
虽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在上海滩多半过得并不如意,但那些大户 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
家的小姐少爷,还是有条件尽 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
享受花花世界的。某些家底殷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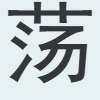 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子弟,为了在戏院包一个名角一掷万金的,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上海的夜总会里,也总是云集着世界各国的佳丽,尤其是俄国大洋马——在苏联建立之后的二十年代,据说有上百万“白俄”逃出国境,在世界各地从事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勾当。正如同苏联解体之后的九十年代。
所以,与中世纪那些纵然身家万贯也过不上好 子的悲惨富
子的悲惨富 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相比,民国年代躲在租界里的中国富豪们,多少还是能够活得更潇洒的。唯一的麻烦是……钱从哪里来?
北洋政府时期,虽然北方内战不断,但江浙和上海的经济还算繁荣,企业家的 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
子尚属滋润。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名义上虽然进 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
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但由于洋货的大举倾销,以及海外市场在大萧条之中的急速萎缩,又没有保护 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
关税,上海的工厂反而纷纷 产,投资实
产,投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