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思衡心道,我如果是个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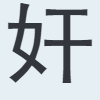 臣,那真的会是祸国殃民的坏,还好还好,他的良心仍然活蹦
臣,那真的会是祸国殃民的坏,还好还好,他的良心仍然活蹦 跳。
跳。
皇帝听罢仍是不肯表态,他何尝不知只有自己的妹妹无时无刻不与自己是一条心?但首先重用皇族,便会引 非议,更何况这皇族还是一位公主?怕是有
非议,更何况这皇族还是一位公主?怕是有 就要拿外戚之事来做文章……
就要拿外戚之事来做文章……
等等,外戚?
长公主没有成家育后,何来外戚之有?
两个脑子高速极限运转的君臣飞快对视一眼,卓思衡点点 ,仿佛在肯定皇帝顿悟的想法一般——当然他不知道皇帝此时想到了什么,不过看眼也知道是意识到非常重要的事,这种时刻,卓思衡认为应该对领导的一切顺势念
,仿佛在肯定皇帝顿悟的想法一般——当然他不知道皇帝此时想到了什么,不过看眼也知道是意识到非常重要的事,这种时刻,卓思衡认为应该对领导的一切顺势念 进行充分的认可。
进行充分的认可。
皇帝心想卓思衡定是预料到这一点,才愿意举荐长公主,然而这件事面对的困难还太多,他虽然需要自己 的坚实助力,也不好为此引发朝局的震
的坚实助力,也不好为此引发朝局的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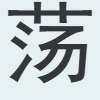 ,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妹妹能够拥有一定权柄,将来的事……即便是托孤辅政,自己也只信得过她。
,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妹妹能够拥有一定权柄,将来的事……即便是托孤辅政,自己也只信得过她。
“你举荐长公主,只有此意么?”皇帝问道。他心中又有了另个想法,卓思衡的妹妹在自己的妹妹麾下编书作传,若是长公主得到实际权柄,他是否有在通过此等方式让妹妹也因此受益,进而使家族荣光?
平心而论,以卓思衡的家族,无需这样的手段,只靠他自己足矣踵事增华,但他如果没有自己的好处,又何必如此唐突?
皇帝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自然不是,臣举荐长公主,也有为学政之革下步排铺之意。”卓思衡通过问题提问的角度敏锐察觉到皇帝的警惕,于是将原本准备的下个论点延后,而最后一个足够有说服力且能让皇帝放松的构想提前。
“你之前向朕保证和奏报之事均已实施,还有什么是未曾言明的?”
卓思衡郑重道:“圣上明鉴,此事并非臣起始所有之意想,这半年中此意逐渐现露,而《 史典》的最终编成促使臣将此希图禀报陛下。臣最后一项学政之变正是……设立
史典》的最终编成促使臣将此希图禀报陛下。臣最后一项学政之变正是……设立 学。”
学。”
皇帝的反应没有卓思衡想象中的大,他很认真得听,似乎也在很认真得思考,许久之后才开 道:“所以你希望长公主有更多权柄,替你便宜从此事?”
道:“所以你希望长公主有更多权柄,替你便宜从此事?”
“也唯有长公主能成此事。”卓思衡觉得自己和皇帝说话都没有这样恳切过,“臣也是有妹妹之 ,于私,臣不愿意看臣妹因身为
,于私,臣不愿意看臣妹因身为 子无法施展才行只能屈居末流;于公,臣自臣妹处得知许多长公主编书以来不让须眉的功绩,臣希望朝野中、陛下侧多能臣
子无法施展才行只能屈居末流;于公,臣自臣妹处得知许多长公主编书以来不让须眉的功绩,臣希望朝野中、陛下侧多能臣 将,此能臣
将,此能臣 将是何
将是何 ,臣并不希望设限。陛下,朝廷和国家都在最需要
,臣并不希望设限。陛下,朝廷和国家都在最需要 才的时候,如果能聚拢天下
才的时候,如果能聚拢天下 子的
子的 心,又何尝不是陛下垂范千古的助力?”
心,又何尝不是陛下垂范千古的助力?”
即便是肺腑之言,也要先摆出利益让皇帝动心。
“吏学尚且存有阻碍,开设 学如果反对之声更甚,你该如何处之?”皇帝并不想表现出自己对卓思衡的提议已经感到蠢蠢欲动,他只是抛出另一个问题。
学如果反对之声更甚,你该如何处之?”皇帝并不想表现出自己对卓思衡的提议已经感到蠢蠢欲动,他只是抛出另一个问题。
“依臣之见, 学倒未必会有吏学反对之声那样多,即便有,也多从腐儒之观外戚之祸大做文章,然而陛下,我朝非但没有过外戚之祸,反倒因公主成事而受益。再加上《
学倒未必会有吏学反对之声那样多,即便有,也多从腐儒之观外戚之祸大做文章,然而陛下,我朝非但没有过外戚之祸,反倒因公主成事而受益。再加上《 史典》里桩桩件件都可以反驳此言,不足为虑。”卓思衡决定给皇帝一点可以彻底放心的定心丸吃吃看,想打动注重利益的
史典》里桩桩件件都可以反驳此言,不足为虑。”卓思衡决定给皇帝一点可以彻底放心的定心丸吃吃看,想打动注重利益的 ,也唯有利益至上的说法能做到了,“陛下,
,也唯有利益至上的说法能做到了,“陛下, 子虽不在朝野,满朝文武功勋却家家有
子虽不在朝野,满朝文武功勋却家家有 子,若
子,若 学能为各家
学能为各家 子提供更高一级可攀升之捷径,众
子提供更高一级可攀升之捷径,众 因受益于此,必然以沉默作为表态,将益处均衡审慎而分,便可更令诸
因受益于此,必然以沉默作为表态,将益处均衡审慎而分,便可更令诸 归心。”
归心。”
卓思衡不给皇帝反应再提问的机会,径直抛出原本前用的论点,加以缀饰,契合方才所言道:“陛下或许会忧心,这些官宦功勋家的 子,亦有力量影响朝局,但陛下也请知晓,这正是臣举荐长公主殿下的原因,试问陛下难道会疑虑长公主的忠诚与耿耿赤忱么?殿下若执掌
子,亦有力量影响朝局,但陛下也请知晓,这正是臣举荐长公主殿下的原因,试问陛下难道会疑虑长公主的忠诚与耿耿赤忱么?殿下若执掌 学,世家
学,世家 子皆于其麾下,她必然是会为陛下与天下尽力守责,若后世愿意效仿此道,也将以天家公主相继可为,亦是长治之略绝非一时之能。远虑近忧臣已经都尽数分明,如何裁断,臣愿谛听陛下的谕令。”
子皆于其麾下,她必然是会为陛下与天下尽力守责,若后世愿意效仿此道,也将以天家公主相继可为,亦是长治之略绝非一时之能。远虑近忧臣已经都尽数分明,如何裁断,臣愿谛听陛下的谕令。”
这次的沉默相对而言短暂许多,卓思衡在心里倒数,十个数还没数完,皇帝便给了他答复。
“朕已知晓你的用心。”皇帝感赞而叹,走下座位至卓思衡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云山,你行事素来为长治天下考虑,朕如何不知?只是此事牵扯略广,朕要考量一番再做决意,朕不是不懂你的意思,而是要权衡许多,你可明白?”
皇帝会为利益动心,也会为利益犹豫,卓思衡早有所料。他并不懊丧也并不失望,只笑而平静得行礼道:“臣侯听圣裁。”
“朕也相信你身为兄长,也有为妹妹所考虑之处,其实朕是兄长,也是 父,朕也希望朕的
父,朕也希望朕的 儿能同儿子一道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这才不负她们生在帝王家,若只是寻常嫁娶,朕又何故命罗
儿能同儿子一道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这才不负她们生在帝王家,若只是寻常嫁娶,朕又何故命罗 史言传身教明德之书明世之典呢?”皇帝
史言传身教明德之书明世之典呢?”皇帝